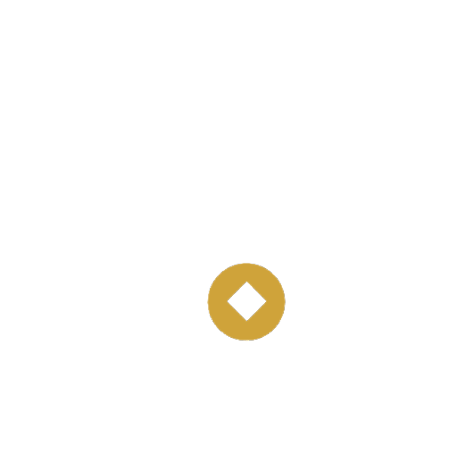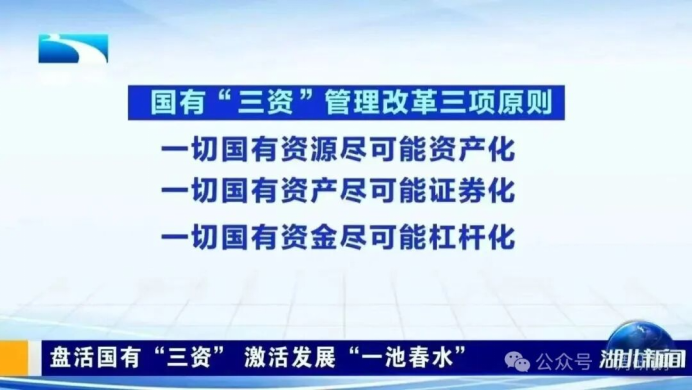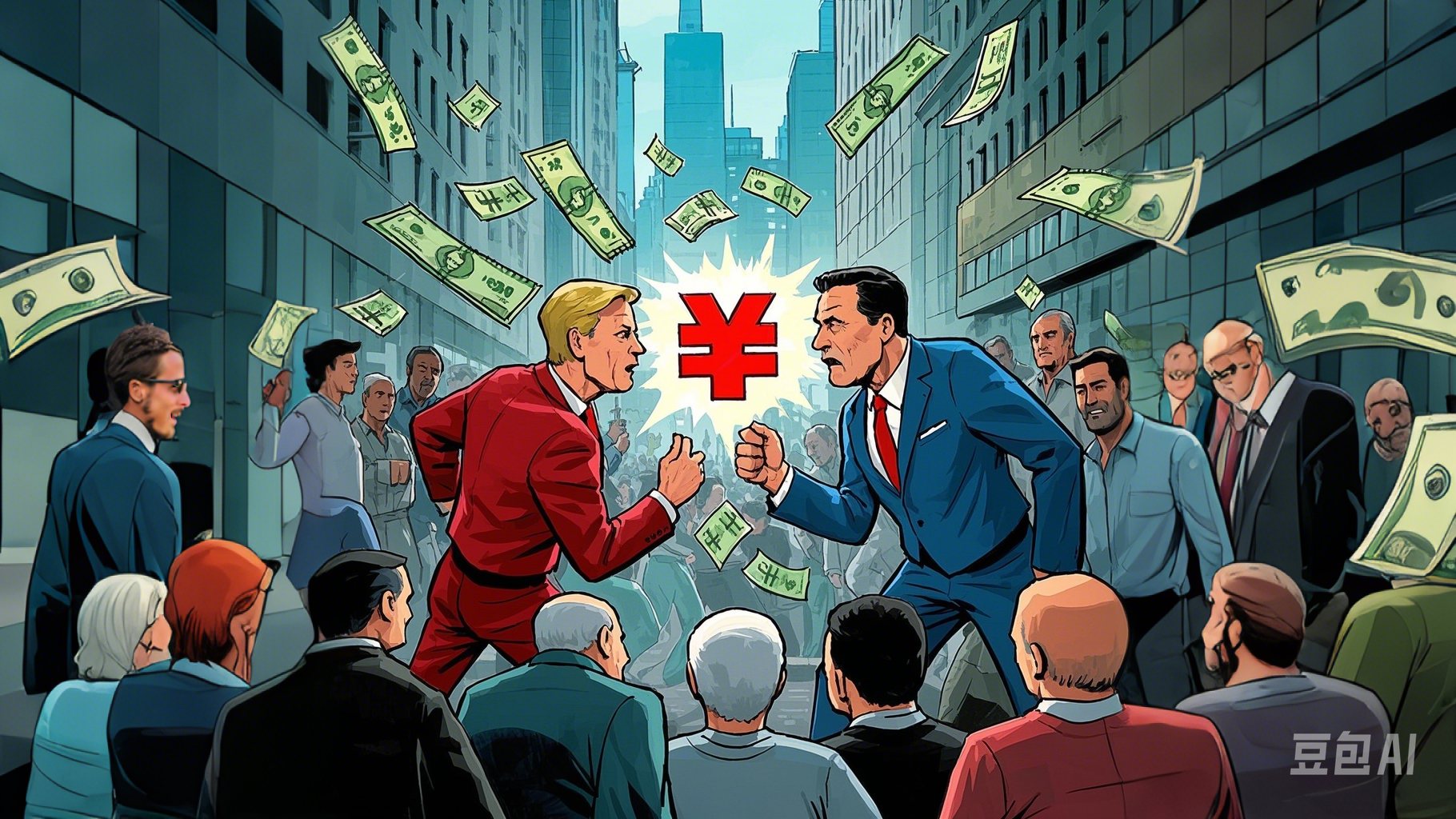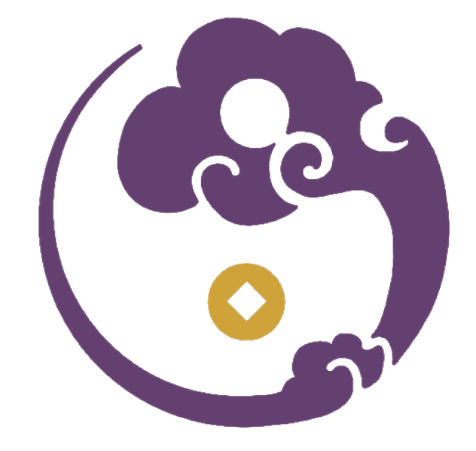资本市场与经济景气度并非线性对应关系
文章作者:张喜芳(公司顾问)、秦兴(高级研究员)
经常有人说,经济不太好,股市起不来。实际上,资本市场与经济景气度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资本市场的繁荣与萧条,是受政策预期、资金流动性、估值高低、产业结构、市场情绪、盈利性、利率与汇率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
简单回顾历史,就可以印证这个结论。经济景气度并不直接决定牛市,但是似乎会影响牛市的长度和高度。
比如1999年的519行情,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当时基本面很不好,通缩压力高企,经济低迷,国企下岗潮。当时,政策上围绕降准降息、启动房改、搞活资本市场展开。上证综指累计涨幅114%,时长25个月。

再如2007年的大牛市,在此之前的2001-2005年,中国在加入WTO后,经济是加速高速增长,但因为股权分置问题、国有股减持等影响信心,却经历了四年持续下跌。最终由股权分置改革落地引发,公募基金开始大量发行推动,A股估值修复驱动,同时伴随着上市公司业绩持续提升,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周期和资源类行业获得4-5倍涨幅。上证综指从998点涨至6124点,涨幅513.6%,时长28个月。
再如2015年牛市,当时经济增速开始下台阶,但随着“新国九条”发布,央行开启降息、沪港通开通、房地产棚改货币化、以及产业层面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仍然爆发了牛市,上证综指涨幅达160%,持续11个月。
可见,资本市场,本来就是预期与现实的博弈,而非完全跟随现实,终极逻辑又是与时间的博弈。可以说,市场稳步发展的超长期根基在经济(如上证指数自1990年100点至当前约3400点约34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9%,期间我国实际GDP和名义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8.5%、13.4%),但牛市的根基却在于极度低估,只要超长期内GDP还在增长,就总是会存在牛市,即便不是全面牛市,也肯定有各类新兴行业的结构性牛市,如2019-2021年间的结构性牛市中,上证指数虽然未创新高,但沪深300其实已超过了2015年高点,而显而易见我国当前GDP增速仍位居全球前列,同时我国在各类新兴行业科技创新和蓬勃发展上也明显占据一席之地。
再看国际上,美股历经了长期牛市,其股市回报与经济增速的“脱钩”也比较明显,美国GDP体量大,但增速并非全球最高(1900-2019年实际GDP年均增速约3%),而股市年化回报率达6.5%,远超高增长的日本(2.8% GDP增速,4-5%回报),其核心在于美国企业盈利全球化(如苹果全球产业链)和美元流动性优势。而日本与德国也经历过经济低迷中的股市逆袭,日本在1990年代后经济长期停滞,但2012年安倍经济学推动日股走出慢牛,2024年GDP排名下滑至第四的背景下,日经指数仍创历史新高。德国在2023年经济受能源危机冲击,导致GDP连续两年转负,但DAX指数因企业盈利韧性(如制造业出口)等环境创历史新高。

因此经济“不好”,也可能催生牛市,主要看是否有驱动因素。
第一类驱动因素是流动性宽松与政策刺激。比如,A股在政策托底(“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推动资金从存款转向股市,就形成过流动性驱动的修复性上涨。再比如,美国2008年后量化宽松,在经济衰退期美联储释放天量流动性,标普500指数2009-2021年上涨超400%。
第二类驱动因素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全球化红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完成产业升级(半导体、汽车),虽经济增速下降(4.1%),但股市回报(5.66%)反超GDP增速。而印度经济GDP增速常年在4%-8%之间不稳定波动,但股市在2020年后迅猛上涨,4年间加速翻倍,其主要受IT外包、医药等特色行业企业盈利增长驱动,而非单纯GDP扩张。
第三类驱动因素是市场情绪与叙事逻辑,就是所谓的信心和想象空间。比如A股今年宏大叙事就包括AI、机器人等产业热点,被提升至“国运”高度,推动市场情绪脱离短期经济数据。再如90年代末,美国市场互联网概念脱离盈利基本面,但流动性充裕、信心充足支撑纳斯达克指数飙升。
所以,经济与股市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多维逻辑,经济高增长并非牛市的充要条件,流动性、政策预期、产业结构升级、全球化能力等因素可能更直接驱动股市,尤其在金融深化与资本开放的经济体中,股市的“晴雨表”功能更多映射资本博弈而非实体经济。
——短期看预期与流动性:政策宽松或危机救助可推动“水牛”(如中国2014年、美国2009年),与经济现实无关。
——中期看盈利转化:GDP增长需转化为企业盈利(如韩国产业升级),否则高增长难支撑牛市。
——长期看制度与全球化:美股长期优势源于美元霸权与企业全球化布局,日股依赖货币宽松与企业改革。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了,当前与历史不同了,现在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分水岭,美国千方百计步步围堵中国,打压中国科技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赢得过,害怕国运从此回落,不敢相信周期会再来,这种悲观看法也常从投资者口中听到,不妨从更大更长的视角上来看看,坚定排除这种悲观,以正信念。
先举个例子,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现在我们从历史后视角看会觉得其理所当然,但要知道,《论持久战》正是在当时抗战极其艰难,刚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从武器、国力等各方面看得见的硬件实力上与敌人都有巨大差距,社会大众充满极度悲观情绪,甚至部分同志也无法坚定信念,认为很可能要亡国,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毛主席纵贯古今的《论持久战》。
不妨对比一下,《论持久战》中的一大论据凭靠,即“中国土地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潜在战略纵深人力物力资源充足”,与当前习主席常提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是不是如出一辙?而去年盛行当前仍存的国运下滑论、国内经济周期一去不复返、大A牛市不再论,又与当年的亡国论何其相似?这不是巧合,其中蕴含的哲学本质是一致的,同样的因素在周期的关键时刻发挥着相似的作用,也如俄罗斯领土上希特勒重蹈拿破仑覆辙一般,周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以中美关系变化为转移的人类发展基本规律,《论持久战》映射到当今中国经济和股市问题上,也可以来一个“论经济周期必复苏、A股牛市必再来”。

再看美国股市。看似从2009年后,美国一直在牛市中,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后续的涨幅掩盖了当时的熊市,其实A股2015年、2022年跌入熊市时,美股也同样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再往前回顾,A股和美股也一直都在同样的周期中,其中每次牛市的顶点时间都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牛市的起点不一样而已,这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股市里的映射。
当我们从整个人类发展规律的基本哲学角度来看,事情会变得更加清晰:即只要人类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周期就会不断循环前进,经济周期、科技周期、股市周期在中美之间的互相影响促进,也永不会断绝。
——自古以来,全球就是在不断的交融互相影响促进,谁能想到我们日常吃的土豆、红薯、玉米都是自国外传来,现代历经几十年深入发展的全球化,更使得这种交融影响快速触达无处不在,当下全球化深度交联、互有长短补充的客观现实已不可能被中美关系变化所逆转,美国对我们的技术打压只能是暂时、局部的,阻碍不了我们的进步和突破,这是人来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在当今社会快模式下,这种规律并不需要在跨越很长的周期里才能体现,而是按日、按月、按年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试看DEEPSEEK即可见。美国打压的,正是我们未来有极大发展前景的,也是我们未来的投资主线。
——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投资大师,如巴菲特、彼得林奇、霍华德马克思、约翰邓普顿等等,都常说到“不去预测宏观经济”或“不以宏观预测为基础来做决策”,那如何做呢?霍华德马克思在去年的一份备忘录里有一句精辟的解释,可以总结他们所有人,即“我们通常假设经济总会往常态回归,我们主要只是观察市场情绪,而非复杂的经济数据分析”,这就是周期,也是巴菲特所所谓“不要靠做空美国发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在美国,美国确实代表了近现代来全人类最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美国股市历经周期能够不断创新高的原因。但中国又何尝不是在快速发展,在国际经济科技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呢?要知道,自古以来近代以前几千年,中国都是全球GDP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当今美国投资大师们的经济周期论在2000年前的中国就有了,即春秋时范蠡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贱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中国在数千年的一轮轮周期中引领全球发展(包括经济与科技),又在改革开放后,能快速抓住全球化大周期、历经一轮轮小周期,发展到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中心,这对有着超长历史力量底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中国来说是有必然性的,连美国也认为中国是有史以来全球唯一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因此,当前恰恰不是对国运周期悲观存疑的阶段,相反未来恰恰是中国可能诞生巴菲特的阶段。

所以,总得来说,目前我国三年经济下行周期结束底部确立进入逐步复苏,未来经济上行周期必将会到来,而资本市场新一轮牛市周期已经在924行情后诞生,并非线性对应经济周期节奏,且中美股市联通律(历次牛市顶点一致,但A股牛市起点晚于美股3-5年,期间总是美股迭创新高/A股跌创新低)仍在发挥作用,自2022年10月开始的美股新一轮牛市(AI牛市)已经在924行情中传导到A股,历史来看,只要A股不新高,美牛就不停,只要美股不熊,A牛就终会与美牛在顶峰相见。当前宜顺势而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未来几年我们也可能见证一个转型的不寻常的更持久的牛市,而2025年的当下,趁着市场大众仍处在半信半疑中,正是积极布局加大播种的好时节,风物长宜放眼量,一道携手共进,守正用奇、行稳致远!